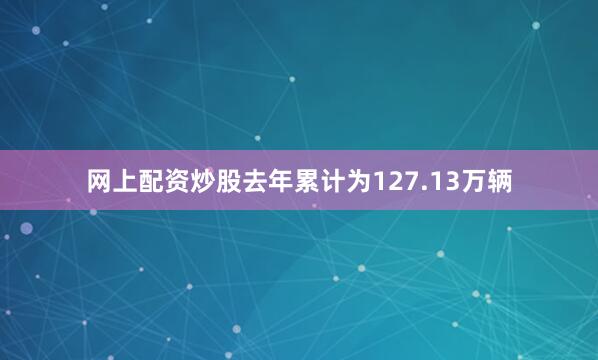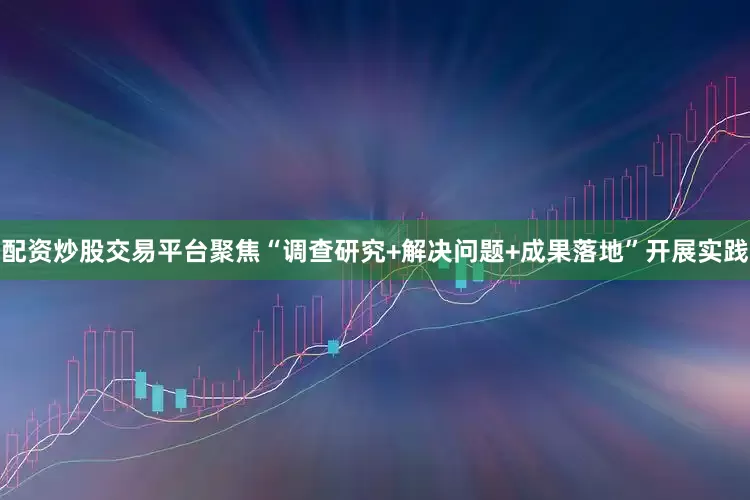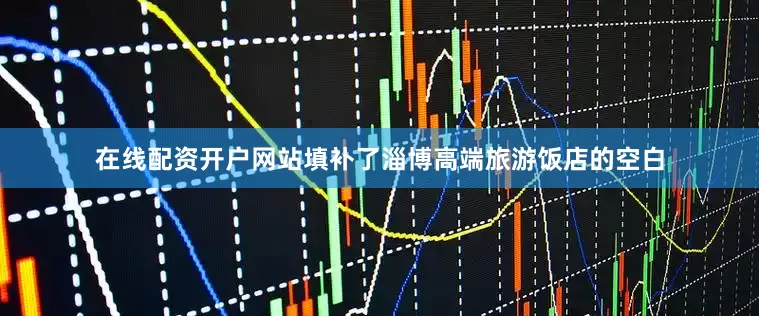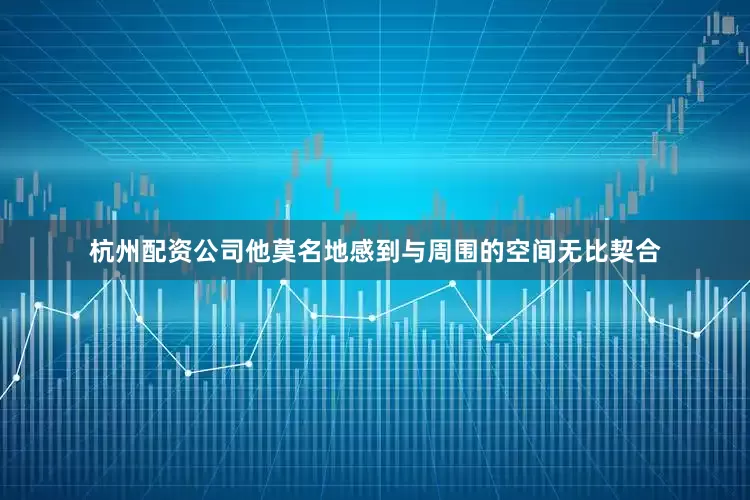长安大戏院的后台,82 岁的刘长瑜拄着拐杖,看着镜中自己的白发。化妆师想给她多抹些发胶,她摆摆手:"不用,李铁梅的辫子要松松的才像。" 当《红灯记》的前奏响起,她颤巍巍地整理好红布衫,一步一步走向舞台 —— 这个曾被印在火柴盒、暖水瓶上的 "全民闺女",用一辈子的坚守,让京剧的光芒穿透了岁月的尘埃。
一、火柴盒上的 "李铁梅":寒冬里练出的经典
1964 年的北京,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,中国京剧院的排练场没有暖气。22 岁的刘长瑜穿着打满补丁的练功服,双手举着竹篮,保持着 "提篮小卖" 的姿势,一站就是两小时。指尖冻得通红发紫,她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,嘴里反复哼着 "我家的表叔数不清",直到唱腔的每个转音都精准得像用尺子量过。
展开剩余90%这是《红灯记》排练的第三十七天。此前,剧团里十几个女演员都试过李铁梅这个角色,要么少了少女的灵动,要么缺了革命者的坚毅。领导们急得团团转,有人小心翼翼地提议:"要不,让刘长瑜试试?" 这话一出,排练场瞬间安静 —— 谁都知道,这个天赋出众的姑娘,因为父亲曾被误判为 "汉奸",一直被晾在角落。
刘长瑜抓住了这个机会。她把铺盖搬到排练场,白天跟着武生练身段,晚上对着镜子抠眼神。为了表现李铁梅 "眼中有火" 的坚定,她在结冰的湖边一站就是清晨,盯着朝阳练眼神,睫毛上结着霜花也浑然不觉;为了把 "痛说家史" 那段唱得撕心裂肺,她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,一遍遍回想母亲讲述的家族苦难,直到嗓子哑得说不出话。
有次排练到深夜,她累得趴在桌上睡着了,手里还攥着剧本。同事悄悄给她盖上棉衣,发现剧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:"此处眼神要左顾右盼"" 这个动作幅度再小些 ""唱腔要先抑后扬"。这些带着体温的字迹,后来都变成了舞台上的高光时刻 —— 当李铁梅举起红灯,那句 "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" 的唱腔,既有少女的清亮,又有战士的铿锵,台下观众的掌声能掀翻屋顶。
1971 年,《红灯记》电影上映,刘长瑜饰演的李铁梅成了全民偶像。扎着乌黑麻花辫、穿着红碎花布衫的姑娘,不仅出现在电影院的海报上,还被印在火柴盒、搪瓷缸、暖水瓶上,走进了千家万户。新疆的边防战士写信来说:"看到您举红灯的样子,我们守边疆更有劲儿了;农村的知青寄来照片,背后写着" 您是我们的榜样 ";还有大爷大妈托人说媒,想把儿子介绍给" 铁梅姑娘 "。
可没人知道,镜头里那个眼神明亮的李铁梅,正经历着人生最黑暗的时刻。拍摄期间,她每天收工后都要往医院跑 —— 新婚三个月的丈夫,正躺在病床上与肺癌搏斗。有次录 "我家的表叔数不清",她唱到 "没有大事不登门" 时,突然想起丈夫咳血的样子,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,导演喊停后,她躲在布景后面哭了整整半小时,再出来时,眼睛红肿却眼神更亮:"再来一条,我知道该怎么唱了。"
二、两段婚姻里的悲欢:从丧夫之痛到相濡以沫
刘长瑜的第一段婚姻,像一出仓促落幕的折子戏。1964 年春天,她和戏曲学院的学长举行了简单的婚礼,婚房里没有像样的家具,墙上贴着两人的戏装照:她是《春草闯堂》里机灵的丫鬟,他是《长坂坡》中威风的赵云。这对金童玉女原本约定,要在舞台上演一辈子夫妻,可婚后三个月,丈夫就开始咳血。
拿到 "肺癌晚期" 诊断书那天,刘长瑜正在排《红灯记》的 "赴宴斗鸠山"。她把诊断书塞进戏服口袋,强忍着眼泪演完铁梅怒斥敌人的戏,谢幕时腿一软差点摔倒。同事要扶她,她摆摆手:"没事,是动作太投入了。" 可一到医院,看到丈夫瘦得只剩一把骨头,她再也撑不住了,趴在床边哭道:"咱不演了,我陪你治病。" 丈夫却摸着她的头说:"铁梅不能没有你,好好唱戏,就是对我最好的交代。"
那四个月,她像个陀螺连轴转。白天在排练场练得浑身是汗,晚上在医院给丈夫擦身、喂药;为了赚医药费,她接了下乡演出的活儿,在颠簸的拖拉机上背台词,在油灯下记唱腔。有次在河北农村演出,她刚唱完《红灯记》,就接到医院电话说丈夫病危,她连夜坐卡车赶回北京,还是没能见到最后一面。
丈夫走在九月的雨夜,临终前只说了句 "好好唱戏"。刘长瑜穿着戏服守在灵前,红布衫被雨水打湿,贴在身上冰凉。剧团里开始传闲言碎语,说她是 "克夫命",没人愿意和她搭档,食堂里她总是独自坐在角落。直到有天,武生演员白继云端着餐盘坐在她对面:"别听他们瞎掰,我陪你排戏。"
白继云比刘长瑜大三岁,是剧团里有名的 "拼命三郎"。他看着这个在舞台上闪闪发光、生活中却孤单落寞的姑娘,心里不是滋味。她练身段没人搭手,他就穿上戏服当配角;她嗓子哑了,他每天早上去后山采野菊花泡成茶;她被观众寄来的 "求爱信" 烦扰,他就帮忙整理信件,只留下请教艺术的内容。
1968 年冬天,白继云用攒了三年的粮票换了一条红纱巾,塞到刘长瑜手里:"我知道你心里苦,以后有我呢。" 这条在当时比钻戒还珍贵的纱巾,让刘长瑜想起了丈夫曾给她别过的绢花,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他们的婚礼比第一次还简单,只有两床新被褥,可刘长瑜觉得,这才是真正的家。
婚后的白继云,成了她最坚实的后盾。他主动从台前退到幕后,当起了 "家庭主夫":她演出晚归,他总能端出温热的艾草泡脚水;她的彩鞋磨破了,他连夜用针线补好,还在鞋底加了层软布;拍《红灯记》电影时,他每天骑车两小时去片场,只为给她带一壶润喉的胖大海。有次刘长瑜发烧到 39 度,硬要去演出,白继云背着她去剧场,在后台帮她化妆、递水,演出结束后又背她回家,一路走一路说:"以后不许这么拼了,你的命比戏重要。"
1975 年,刘长瑜在事业巅峰时生下儿子。月子里,白继云学会了换尿布、冲奶粉,还按照老方子给她熬小米粥。看着丈夫笨拙却认真的样子,刘长瑜笑着说:"你这武生,现在成了 ' 月嫂 ' 了。" 白继云挠挠头:"能伺候李铁梅,是我的福气。" 这份相濡以沫的温情,成了她后来几十年艺术生涯的底气。
三、从 "三姨太之女" 到京剧头牌:苦难里开出的花
刘长瑜的童年,像一出压抑的苦戏。1942 年,她出生在北平市长周大文的府邸,是父亲与三姨太的女儿。在这个有 14 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里,她像个透明人,吃不饱饭是常事,穿的衣服都是姐姐们剩下的。唯一的慰藉,是父亲收藏的京剧唱片。夜深人静时,她躲在被子里听《玉堂春》《红娘》,跟着唱片咿咿呀呀地唱,那些婉转的唱腔,成了她对抗孤独的武器。
1949 年,父亲被关押,母亲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了周家。7 岁的刘长瑜,偷偷把一张《玉堂春》的唱片藏进包袱 —— 这是她从大宅院里带走的唯一念想。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,她靠在街头唱片机旁听戏,把歌词记在烟盒背面,练就了过目不忘的本事。
1951 年,中国戏曲学校招生,9 岁的刘长瑜背着母亲报了名。考场上,考官们看着这个瘦弱的小女孩直摇头,可当她开口唱起《女起解》,清亮的嗓音和精准的身段让所有人都惊呆了。主考官荀慧生摸着胡子说:"这孩子,是吃京剧这碗饭的料。"
进了戏校,刘长瑜才知道什么叫 "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"。寒冬腊月,她凌晨四点就去操场练毯子功,翻跟头翻得浑身是伤;盛夏酷暑,她嘴里含着石子练发音,嘴角磨出了血泡也不吭声。别的同学休息时,她在练功房对着镜子练眼神,把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里的小姐们都琢磨个遍。有次练 "卧鱼" 动作,她因为体力不支摔倒,膝盖磕出了血,却爬起来继续练,直到能稳稳地在台上 "卧" 三分钟。
1962 年毕业演出,20 岁的刘长瑜一人分饰两角:《卖水》里活泼俏皮的花旦,《宇宙锋》里悲愤决绝的青衣。她踩着三寸厚底鞋,先把花旦的娇憨演得活灵活现,转场十分钟后,又把青衣的悲戚唱得催人泪下。台下的荀慧生激动地拍案叫绝:"这孩子,把我的荀派精髓都吃透了!"
可就在她崭露头角时,父亲的历史问题成了 "污点"。剧团里评先进没她的份,重要演出不让她上,有人甚至在背后说她 "根不正苗不红"。那段时间,她白天在排练场打杂,晚上偷偷练戏,把委屈和不甘都藏在唱腔里。直到《红灯记》选角,她才抓住命运递来的橄榄枝 —— 正如李铁梅在戏里唱的 "千难万险何所惧",她用实力证明,艺术从不问出身。
走红后,刘长瑜从未忘记自己的来路。她把演出费攒起来,资助了十几个贫困的戏曲学生;下乡演出时,她会给农村孩子教身段,说 "只要喜欢京剧,我就教";遇到有天赋却家境贫寒的学生,她不仅免学费,还承担了他们的生活费。有人说她傻,她却笑着说:"我当年要是没人帮,哪有今天?"
四、82 岁仍传灯:把京剧的火种播向未来
如今的刘长瑜,早已从舞台中央退到幕后,但她的生活依然围着京剧转。每周三上午,她会准时出现在中国戏曲学院的排练场,给 00 后的学生们上课。82 岁的她,拄着拐杖示范《卖水》里的 "表花" 身段,脚步虽然缓慢,每个手势、每个眼神却依然精准:"这里的扇子要转得像蝴蝶,眼睛要跟着扇子走,才能演出小姑娘的灵动。"
疫情期间,她学会了用手机直播授课。对着镜头,她把 "提篮" 动作拆解成十个步骤,从手腕的角度到肩膀的力度,一点点讲解:"京剧讲究 ' 圆',每个动作都要像画圈,不能直来直去。" 有次演示 "卧鱼" 时,她没站稳摔了一跤,学生们在屏幕那头急得喊 "老师别动",她却爬起来笑着说:"没事,你们看清楚了吗?刚才那个角度不对,应该这样......"
她的学生里,走出了赵玉华、管波、耿巧云等名角,个个都是当今京剧舞台的中坚力量。管波说:"刘老师教戏,不仅教身段唱腔,更教怎么做人。她总说,台下做好人,台上才能演好戏。" 耿巧云记得,自己刚学李铁梅时总找不到感觉,刘长瑜带她去参观革命纪念馆,说:"你得知道铁梅为什么要举红灯,才能把那股劲儿演出来。"
除了教学生,刘长瑜还在整理自己的艺术笔记。那些泛黄的本子上,记着《红灯记》《卖水》等剧目的细节:"李铁梅的辫子要甩得有力量"" 春草的眼神要带点俏皮 "。她计划把这些笔记出版," 给后辈留点有用的东西 "。有人劝她歇歇,她却说:" 只要还能动,我就教下去。京剧这门艺术,得一代代传下去。"
2023 年重阳节,长安大戏院为她举办了艺术生涯纪念演出。当《红灯记》的前奏响起,82 岁的刘长瑜再次站上舞台,虽然步履蹒跚,唱起 "我家的表叔数不清" 时,声音依然清亮。台下坐满了三代观众:白发苍苍的老戏迷跟着哼唱,中年人举起手机记录,孩子们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 —— 这束从火柴盒上亮起的光,经过半个多世纪,依然温暖明亮。
演出结束后,有记者问她:"这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?" 刘长瑜看着后台来来往往的年轻演员,笑着说:"不是演了李铁梅,而是看到这么多孩子喜欢京剧。只要有人学、有人演,京剧就永远有生命力。"
从被印在火柴盒上的全民偶像,到默默传艺的京剧教育家,刘长瑜的一生,就像她演了一辈子的红灯 —— 在黑暗中坚守光明,在风雨里传递温暖。如今,这盏灯交到了年轻人手里,而她,依然站在灯火阑珊处,笑着看京剧的光芒,照亮更远的未来。
发布于:江西省股票金融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